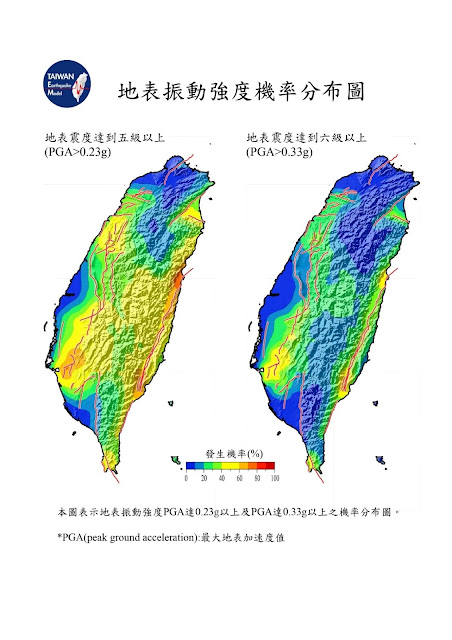文/阿樹
《震識:那些你想知道的震事》副總編輯
地震真的無從預測嗎?目前純就科學的角度,的確還做不到。然而相關領域的科學家卻未曾放棄對地震前兆的研究。一份由美國西北大學為首的地震團隊最新公布的長微震研究結果,讓未來的地震預報(forecast)見到一線曙光,最特別的是,這項由跨越多國學者、 八個研究機構合作作出的研究,採用的地震資料來自於臺灣。
什麼是長微震?
在細談本篇研究之前,我們必須先認識一種特別的地震現象:長微震 (tremor),如果用google 搜尋”tremor”,你會看到這個名詞在醫學上所指的是一種顫抖症,換句話說長微震和我們一般感受到的地震不同,它多半只會產生極微弱且連續的地震波,不至於造成地面搖晃。這種微震在火山區一般被認為和岩漿或熱水活動有關,稱之為火山長微震 (volcanic tremor);而如果是在非火山地區,則多見於板塊隱沒帶的邊界深處,一般稱為非火山長微震 (non-volcanic tremor) 。長微震屬於慢地震的一種(註1),慢地震的震源一般位於快速破裂的普通地震和持續移動的無震滑移 (註2)間的斷層帶上。
非火山長微震首次被偵測到,是在2002年日本西南部的南海(Nankai)地區,之後在全球主要板塊交界處都被陸續偵測到這種現象。而台灣最早則是在2008年才在中央山脈南段發現到觸發型長微震(triggered tremor),其後學者才開始展開對台灣自發型長微震(ambient tremor)的研究(註3)。
近十年來地震學家開始對長微震產生高度興趣,主要原因是長微震對微小的應力變化極為敏感。例如長微震可以被地球潮汐或數千公里之遙的地震產生的極小應力變化所誘發,此力道遠小於一個大氣壓力或約等同用手掌互相推擠的力量。科學家研判透過觀察長微震,有機會能推測鄰近斷層發生地震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研究到底有什麼值得關注的地方?
這篇發表在美國地球物理研究期刊(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olidEarth)上的研究,主要在分析2010年3月高雄規模6.4的甲仙地震前後,能否偵測到長微震的異常變化(圖1)。該研究的第一作者趙子凱(Kevin Chao)為美國西北大學的數據科學家(Data Scientist),他與多名國內外著名的研究團隊(註4)合作發現,該次地震前約2個月和3週前,長微震的模式產生了變化(圖2a綠色部分長微震累加率cumulative tremor rate及圖2b藍色部分長微震現象的再現週期tremor recurrence;垂直虛線與紅線之間),GP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的位移觀測資料也同時出現了巧合的關聯性(圖2a黑色空心圈的觀測值)。
 |
| 圖1,此研究所鎖定的區域與該地區的長微震,星號為較大的地震,其中黃色星號(圖例中以藍色文字標記)是此研究發現與長微震活動有關聯的地震,而黃色圓圈是自發型長微震。圖片來自此研究發表在期刊上的文章(Chao, et al., 2017)。 |
 |
| 圖2,此研究的長微震變化行為。(a)為長微震累加率和GPS位移關係。(b)為長微震再現週期的變化。圖片由研究第一作者趙子凱提供。 |
過去幾年早有科學家觀察到大地震前長微震會產生異常的現象,但大多僅從分布上探討,而這篇研究則成功地連結了地表GPS的觀測資料,利用第二種資料的佐證,讓我們得以進一步分析這些長微震和大地震的的關聯。研究中除了選擇2010年甲仙地震的主震(圖3a),也選了其它幾個較大的餘震分析,發現在隔年一月底規模4.2的甲仙餘震發生之前,也可觀察到長微震異常的現象,GPS訊號中同時也看到位移方向的變化(圖3d)。不過,在另一個2010年7月規模5.7的餘震前後卻沒有發現微地動異常的情況,研究團隊傾向認為這次地震距離主震時間較近,長微震的分布可能還是受到先前甲仙主震的影響(仍較活躍),而到了隔年其影響較低,而使得規模5.7地震震前產生的應力變化無法影響到長微震的活動度。
 |
圖3,此研究所觀測的五次地震與長微震活動/GPS資料的關係。圖例與圖2(a)類似,綠色線段為長微震累加率,長條圖為長微震的活動程度(持續時間),白色空心圓圈為GPS的位移資料。圖片來自此研究發表在期刊上的文章(Chao, et al., 2017)。
|
有些研究慢地震的科學家希望把長微震及慢滑移事件(slow slip event, 亦為慢地震的一種)作為偵測地下應力狀態的應力儀(stress meters),只要找到方式量化此種現象,並找出與大地震有規律且具統計意義的關聯性,某程度上就能作短期預測及預報,但事實上統計處理並不容易,就算是這篇研究也還沒辦法完全解決這問題。不過這項研究至少找到兩者之間的關聯,並成功從物理上解釋結果,仍然在某種程度上提高短期地震危害評估的精確度,舉例來說:
- 已知某斷層在未來數年(中期預報範疇)有高機率發生規模6.0以上的的地震,如果其鄰近斷層開始觀察到長微震出現異常,GPS資料也出現異常變化 (甲仙地震當年情況即是如此),則可推論該區域短期(大約數個月內)發生地震的機率高 (當然,類似的地震預報僅在科學研究而非實用階段)。
參與此研究的學者專長領域包括數據科學、地震學、大地測量學、地球物理等等,我們也可想見未來研究地震預測的議題會需要更多跨領域的專家攜手合作。雖然這項研究還稱不上已找到解決地震預報的最佳方法,但卻是一項結合力學理論和觀測統計的新嘗試。
註1:一般地震持續的時間長度約數十秒到數十分鐘,而慢地震(slow earthquake)的長度則可長達數小時到數個月不等,也就是能量的釋放方式較為和緩,但儀器仍可觀測到訊號。慢地震可簡單區分為兩種類別:一是能被地震儀記錄到的長微震、低頻地震(low-frequency earthquake)及超低頻地震(very low-frequency earthquake);另一類是僅能被GPS或其它大地測量儀器觀測到的慢滑移事件(slow slip event) 。
註3:臺灣的長微震的研究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研究團隊為主。
註 4:共同合作單位包含了我國的中央研究院、中央氣象局、成功大學,日本東京大學、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曼菲斯大學及美國地質調查局。
參考文獻:
Chao, K., Z. Peng, Y.-J. Hsu, K. Obara, C.
Wu, K.-E. Ching, S. van der Lee, H.-C. Pu, P.-L. Leu, and A. Wech (2017),
Temporal Variation of Tectonic Tremor Activity in Southern Taiwan Around the
2010 ML6.4 Jiashian Earthquake, J. Geophys. Res. Solid Earth, 122, 5417-5434,
DOI:10.1002/2016JB013925.